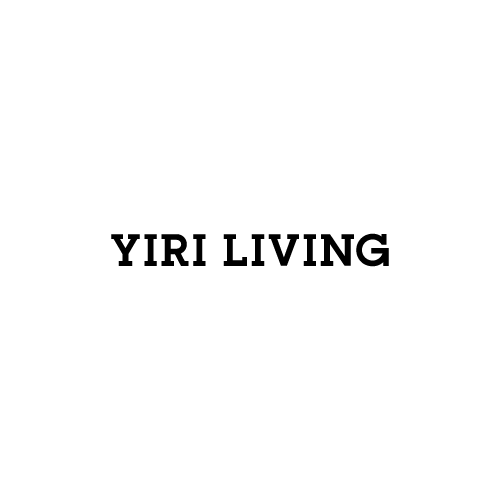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以前只要是每天有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比如與朋友約定的聚會,或某個等了很久的包裹到了。現在會覺得,吃好睡好,早上拉開窗簾看見好天氣,就是美好的一天。」 — 黃斐柔
疫起:視訊對話
五月,忽然地,新冠肺炎(COVID-19)就在我們的島上蔓延開來,完全的猝不及防。在每天不斷翻增的確診病例數中,全國以三級警戒抗疫,不聚集,少出門,待在家,盡可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繁忙的城市,街淨巷空,一剎時靜止如乾涸的河流。
繼一片口罩的呼吸屏障,日常的行動也進入受限制的階段。為了防疫,乖乖繭居,保全自己,似乎已是最積極有效的配合辦法。無法南下彰化,約定的採訪,不得已改弦易轍。
所謂隨機應變,既無法親面會晤,那就像居家辦公的線上會議般,與斐柔開啟了視訊對話。還記得那日,星期五下午,梅雨鋒面臨近,天空滿滿的灰雲鬱積,驅散一些立夏後迫不及待的熱意。

那個長髮飄飄的雙魚座女生
社群媒體異國背景的照片裡,一頭及腰長髮飛揚不羈的斐柔,高挑明亮,披掛一身民族風的衫裙,很波希米亞。彷彿一切冷靜,無有所繫,流浪的吉普賽人。而散文集中的她,纖細敏感,有著「或許,讓我們長大的並不是年歲,而是生命際遇中的萬千變化。」此般的透澈,也有「當這宇宙,要讓你學習世間的一切道理之時/它便會將一切,託付給你以外的另一個靈魂」那般的多情。
熟悉的朋友都形容斐柔為人隨和,脾氣好,在群體之中,她大多沉默,旁觀周遭的種種發生,好像生活的每個場景都是旅途中一幕幕流動的景色。雖然隨性,也少有堅持,但那並不等於缺乏個性。雙魚座的她直陳自己其實很玻璃心,尤其相信的價值觀一旦遭到挑戰,便會極力捍衛,執拗地想要去說服,去扭轉。像是一種印象反差,平常悶不吭聲的,不鳴則已,一鳴就驚人,深知她這一面的親密伴侶總愛戲謔她像是「氣炸鍋」似的。
國中時期,被當時風靡的藤井樹影響,十五歲花樣年華的斐柔偷偷寫著談情說愛的小說。而作文總獲國文老師青睞,開心之餘,在常常朗誦給全班同學聽的鼓勵下,成就感亦飽滿了自信。然而,身高足有一米七六的她,上了高中,好像既意外又似乎合情合理地愛上籃球,愛上那種團隊合作,一起揮汗如雨的酣暢淋漓。彼時她沉迷運動,在校隊擔任隊長,爾後甚至考進體育學院就讀了一個學期⋯⋯儘管忘了文字,忘了寫作,忘了一度立志的作家夢想,可是,文字早已是埋在內心一顆沉睡的種子,只要一個灌溉的機會,總有一天就會再次萌出土表。
如今,文字不僅在斐柔二十四歲第一次長途旅行時發芽,更綻了繁麗的花。甫出版的首本散文集《荒涼手記》裡,對生病奶奶的牽念告白與旅行的深淺足跡互為經緯,盤根錯節交織出了斐柔啟程、半途與歸返的路線圖。那些經歷,都是對於身體的、精神的,也是心靈上的凝視與叩問。
薄霧瀰漫的清晨
旅行,由風潮演進為普遍的現代顯學,每個人都有偏愛的探訪世界的方式,屬於自己的旅行的意義,但一路以來,除了意義,斐柔更確定的,或許是走得愈遠,她就離家愈近。一如她筆下:「世界給了我那麼多,並非是要我成為一個只有遠方的人。而是這世界的每一個遠方,都讓我成為一個有家的人。」可能,不是所有的離開都是為了回來,也不是每一次再見都是為了再會,因為拉開了距離,因為曾轉過身去,我們才真正肯定了什麼是捨不下的在乎與牽掛。
研究顯示,人的嗅覺記憶遠比視覺與聽覺鏤刻得更深切、更久長,那麼,旅行之所以讓旅人回味無窮,大概就是隱含著一種獨特的「氣味」使然吧。
「第一次出國是與家人跟團到吳哥窟。我永遠記得在巴揚寺親眼目睹佛塔頂上『高棉的微笑』石雕時的震撼,整個人像丟了魂似的目不轉睛。」恰如初戀總是最難以忘懷,斐柔一下子便重返當時,「為了看日出,天未亮,摸黑搭上嘟嘟車。我一直忘不了那個清晨潮濕的空氣、紅土路揚起的煙塵,還有愛睏的昏沉加上初到陌生國度的亢奮心情⋯⋯經過眼前的畫面、竄過鼻腔的各種氣息,都是超級新鮮的感官經驗,那次我感覺自己像是有個『開關』被打開了,應該可以說是一種對旅行的啟蒙吧!」
氣味像是一枚永誌不渝的烙印,不論時光如何荏苒,座標怎樣迷離,我們總能在嗅覺被喚醒的一刻,重溫那鄉愁似的情懷。我請斐柔試著用一種「氣味」描摹旅行,她一臉神遊,仿若又逆入了某個回憶的漩渦,「除了吳哥窟那趟外,有次要搭很早很早的船班去北海道上的某個小島,一踏出旅店,霧氣濛濛,晨露濕答答的空氣撲鼻而來⋯⋯我想那就是旅行的味道,像是整個世界才剛剛甦醒過來、很清新很乾淨的味道。」聽著,我也憶起自己在旅途中那些星光未熄、雀仍酣眠便要上路,透早的空寂時刻。斐柔說她的A Better Day:「以前只要是每天有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比如與朋友約定的聚會,或某個等了很久的包裹到了。現在會覺得,吃好睡好,早上拉開窗簾看見好天氣,就是美好的一天。」看來,就像旅行之樂在於晨,一日之美好也在於晨了。

在旅途中認識陌生的自己
成為旅者以後,斐柔開始游牧般,來回穿梭於他者與自我、理想與現實、獲得與失去之間。她在天涯觸及生活的荒涼,在海角看見生命的孤獨。就像她寫的「我們總在離開歸屬之地後,心才會真正屬於歸屬之地。」那些身在其中,因太靠近而失焦的,都在遠走以後才褪去暗影,呈露了真實的輪廓。
「我很佩服會攝影的人,鏡頭裡的畫面就是他們想要講的故事,快門一按的當下,故事也就完成了。」不擅拍照的斐柔,自覺沒有攝影者臨場的機靈,發達的敏銳度,遲鈍也好,慢熱也罷,寫字才是她構築一趟旅程的方式。就像遠離才能釐清深陷的迷惘,反之亦然,只有返回以後,經過沉澱,混濁的水澄清了,才能好好重新校準在路上時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的跌宕感受。「我不知道每次旅行會遇到什麼樣的風景,也就無法確定將連結到生活或生命中的哪些部分,進而得到反思。寫旅行,我想,就像是一個契機,一個『看看自己這次會得到什麼』的契機。」
那未知,是契機,也如神祕的鼓聲,悠悠忽忽蠱誘得斐柔蠢蠢欲動。世界太遼闊,在途中所有的相遇告別,都是不斷在面對從未發現過的自己。那年,在冰島,手機群組訊息裡,斷續更新著奶奶住院時好時壞的狀況,人在風光無限的異鄉,心卻揪在千里之外的家鄉,但一晚,在極光浮游的穹蒼下,她竟重置歸零般一片空白,充臆胸懷的只是完全的喜悅;而在法羅群島的廣袤草原上,看見羊隻垂首吃草,情不自禁地轉頭對一旁的妹妹自然而然的一句,「我覺得好幸福哦!」⋯⋯她才認識到,原來,自己也能有暫且斷開現實中紛雜拉扯,心無旁騖的能力與狀態。
「旅行有不同的主調,有人追求冒險感,有人獨鍾生活感。」作為旅人,斐柔約莫是與寫字的她一樣抒情感性的。北海道的鐵道之旅,她搭著車,緩緩晃蕩,只管向前,沿途驛站經過,多數滄海一粟般荒蕪,那寂寞啊,如秘境,不被俗世打擾也不需要被什麼安慰。她選擇的停留跟出發同樣沒有理由,一如她也分不清在那無比浪漫的時空之中,慢下來的究竟是時間,還是自己的心?
「人生真的有太多可能。有時候,以為去了很多地方,看過很多風景,覺得世界大概就那樣了、旅行也就是那麼一回事,誤解自己已經懂得一切,但其實在每一趟前所未有的體驗中,往往某個部分的自己都會被不同的思考推翻,然後再重塑。所以到現在,我依然無法明白定義自己的人生到底正朝著哪個方向。」斐柔呵呵笑咧一口皓齒。
疫時:我們終將再次抵達遠方
肺疫殃及全球之後,每個旅人都折翼,無力飛行。不能出國,那就騎機車環島吧!
「在國外,觀點都是很廣大的,但環島,視線就會集中在路邊花草啦、奇怪有趣的路名或村名,每個地方居民的模樣和日常習慣等等小處的細節。」斐柔猶記得第一天在嘉義,向晚,車停稻田邊,打算拍攝一輪大大的金色夕陽。兩個樣子有點兇、做工程的大哥靠近攀談,看著令人有絲畏怯。知悉她與朋友正在環島,迭聲大讚著,覺得非常了不起。離開前,他們堆了滿臉燦爛的笑:「加油,一路小心,Bye-bye!」她覺得心臟被一股溫暖擊中,一個念頭油然而生:一整天的移動也許都是為了與他們的笑容相遇。
沒料到,現下,疫情疾速升溫,連想要回線西老家海邊晃晃都缺乏安全感,更甭說旅行了吧?
「我們還是會旅行啊!」斐柔一派輕鬆怡然,「騎車去文具店跟書店上班的時候,我和妹妹會故意走沒走過的路線,看沒看過的故鄉景致,鄉下的路都很奇怪,小小的,又彎來繞去,偶爾會遇到死巷子,不過也沒關係,旅行不就是這樣的嗎?」我想起斐柔在書裡的一段文字:「我們恣意騎行在小路間,想停下即停下,想轉彎便轉彎,我從不介意迷路於其中。不過,嚴格來說,或許也不能說是『迷路』,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方向。我非常喜歡像這樣的旅行方式,不管我如何選擇,每一條路都會為我帶來一種新的風景。」是啊,只要在路上,無論遠近,什麼型態,都可以是一場旅行。停在哪裡,那裡就是目的地。
若一顆心不停嚮往地搏動著,我們必然會再次出發——去聞聞不同季節的花草香,吹吹陌地的風,看看那些大山,那些大海,那些人與物,那些午夜夢迴,總是在遠方的風景。
*文字 / 陳冠良,圖片/黃斐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