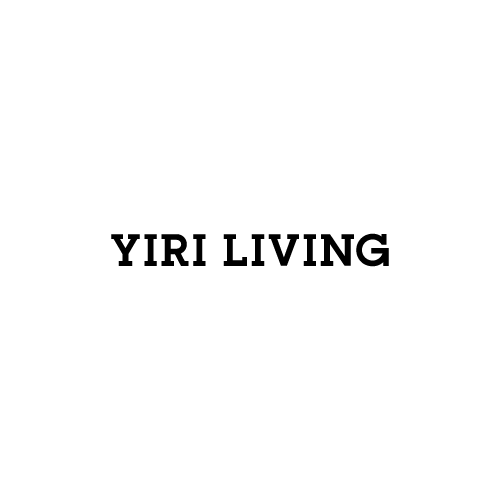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我覺得 A Better Day 就是 A Better World 吧。如果這世界有因為我而變好一點點,彼此不對立,多一些了解,環境也能被更友善地對待 ⋯⋯ 那每天都會是更棒更好的一天。」 —— 蔡祐庭
「不是,那是山澗野花,沒有名字,我卻記得樣子。」
「不是沒有名字,是人類還沒發現。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有了陽光就有植物生長,植物餵養了人類。人類到世界各個角落,為各種植物命名。」——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
山腳下的農場
豔陽天,攝氏三十四度的燒灼感,麻辣燙膚。
虎豹獅象毗鄰而成四獸山,既隱蔽又開闊的「象山農場」沉靜偎在象山腳下的自然保護區裡。漫長光陰,幾番輾轉,從最初名噪一時的人體模特兒與舞蹈家林絲緞老師,到現在掌事的「園藝治療師」蔡祐庭提倡下,才完整了如今提供身心障礙者、藝術統合教育、生態農場與教學功能互為經緯的型態樣貌。該如何定義這樣一個場域?說治療,其實更似安撫慰藉;稱庇護嘛,讓人自主獨立又才是圭臬。就像給你一條魚,不如教你懂得釣一池魚。
鬧騰騰的蟬唧蟲嘶,響徹滿山間,密密無一絲歇喘縫隙。
藤編帽,絳衫亞麻褲,夾著人字拖的蔡祐庭,說話聲線鬆軟,大笑時丹田飽滿。跟隨他閒逸腳步,我們一路相逢被他視為工作夥伴的植物同事們。剛離開「藝統中心」供作自閉症兒童身體開發課程的舞蹈教室,就碰見一籃新鮮油亮的青辣椒,祐庭問頂著斗笠的採收大姐是會辣的嗎?得知屬辣,便嘟噥起可以製成辣椒醬。經過一叢綠,他伸手扭下一片邊緣鋸齒狀的葉,指間搓揉,湊近鼻尖嗅出百香果氣味,那是芳香萬壽菊,徑旁一排林,拉起黃色水管,旋開水龍頭就水花四濺地澆灑起來。緊接著,紅藜之後,是台灣特有種的天然穀物,台灣油芒,它可是大有機會名列世界自然遺產呢,陸續而來的還有香藥草紫蘇、斑蘭葉與左手香 ⋯⋯
來到一塊茂盛豐饒的菜圃前,「這些菜是我們這裡的九位學障青年分組栽種的。他們都是屬於看不出明顯差異的臨界狀態,在職場上易受挫,想領身心障礙補助又相對能力太好而資格不符。雖然賺錢是重要需求,但以他們的狀況,工作的意義不應只是如此,而是每天都有想做的事,生活有重心,感到自己有被需要。這些年輕孩子在這裡種菜勞作,不必成天躲在家,也可以有事情將身心投入,與人互動,過程中,菜園的生機就是他們付出的回饋與體認被需要的價值。現在其中兩個已經是農場正式的工讀生了。」
為自己找一棵樹朋友
步程繼續推前,石板路上,夾道的仍是濃烈的勃勃盎然。祐庭像在介紹家族成員般這裡指指咖啡樹、野薑花與刺蔥,那裡點點葡萄、洛神與金銀花,一見傍園的民居後院裡蹲著熟悉身影,他揮手高喊,「陳媽媽在摘苦瓜啊!」而直到出了「王母區」(藝統中心現址原是供奉瑤池金母的宮廟)的矮柵欄門,還有一株過山香在那兒等著被引見。
越過一個岔路口,我們就進入了農場位於「王爺區」(自然就是其處有座王爺廟)內的「園療中心」。較與「王母區」以服務人們為主的規劃,這裡則將空間還給大自然,維持著植物的高密度與多樣性。
祐庭站定一棵榕樹之下,抬頭望去,仰之彌高,他敞開雙臂,說這棵樹是腳下土地的守護神,大大張開而延伸的枝幹多像一個兼容並蓄的懷抱。面對兩年「疫情生活」以來方方面面的彈性疲乏,從園藝治療的角度,除了蒔花弄草怡情養性,他建議可以就近找一棵健康的、直徑約莫二十公分以上,與自己心靈相應的樹木當朋友。與樹互動,保持連結,祂吸收來自「地水火風空」的五大元素,能夠安定、補充並提升內在的力量。
「樹是有能量圈的,只要靠近了就會對人產生影響。」亦步亦趨祐庭身後,他對植物待以溫柔呵護,咀嚼它們的名字就像在輕喚心愛之人的小名,肖楠牛樟落羽松、茶樹黃荊穗花棋盤腳 ⋯⋯ 看著聽著浸沐著,即便不過初來乍到這片幽林卻倍感親近而自在。那就是一種療癒的感覺了吧!

同理心是一條雙向道
春天時候落成的「象小屋」是進行深層療癒課程的場所。坐在屋裡,外面洶湧的野性氣息,如遠遠退潮的海岸線,剩下無垠的平靜。桌几上,擺著農場自釀的梅酒、梅醋與發酵的康普茶,還有一壺泡著祐庭順手摘回的草葉的水。
很難想像眼前爽朗常笑,對自然與教學侃侃而談的祐庭,曾經否定自己、蔑視自己,不知道怎麼做自己,受困於輕鬱的泥淖。
天生對內在關注大於外界的「內傾人格」,讓他從小就陷在對什麼都格格不入的夾縫之中。當然那時他並不清楚癥結點。直到經過台大心理系被傾聽被溫暖的滋養,才明白了他在想要討好身邊人事又不願委屈自己之間傾斜失衡。經過心理學的訓練,竟使得他對一切保持開放態度,不妄下結論,那也等於釋放了自己——將貼在身上所有「應該怎樣」或「不應該怎樣」的標籤一一撕去。一如成熟樹身上終究會龜裂剝離的老皮。
困難成長的過程,很沉很疲憊,後來被祐庭珍視為孕育的土壤,那賦予他強壯的同理心,「建立有意義的關係是療癒工作很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說,當你之於對方是有意義的,對他才會發生影響力。」若同情是一條單向道,同理別人才能達成溝通,那是一名稱職的治療師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祐庭說的話,乍聽教條,實卻充滿溫度。一段有厚度的關係,並不總是相對等的累積,若非信念,何來堅固基礎。「我覺得 A Better Day 就是 A Better World 吧。如果這世界有因為我而變好一點點,彼此不對立,多一些了解,環境也能被更友善地對待 ⋯⋯ 那每天都會是更棒更好的一天。」我這才發覺那分溫度是從何燃起的。
不算治療,而是扶持
學有專精,祐庭卻全然無心學以致用。不涉入心理臨床工作,主要是排斥問診間裡被規限而隔閡的醫病關係。那樣定時定點「噓寒問暖」的互動,醫者始終旁觀,患者畢竟依附藥物。
不想再作學生,所以不考研究所。當完兵,兜轉一陣,他確定了與孩童相關的工作方向。除了喜歡孩子單純的靈魂,還另有跡可循。大學參加的「手足連心工作站」社團,服務家中有心智障礙兄弟姐妹的一般生。他們可能被忽略,也許被過度期待,社團支持性的輔導,讓他們可以彼此陪伴長大,有些孩子後來甚至也獻身於助人的工作。那時埋下了因,成為兒童雜誌編輯就是長出來的果。平時編務龐雜,而負責的自然科學主題,讓他也必須去上課、聽演講與大量閱讀資料,花費的時間與心力,奠定了紮實的知識基礎,而真正與大自然產生緊密連結,始於登山時的一個難忘體驗。
第一次爬山,便是海拔三千公尺,布農語稱「月亮的倒影」的嘉明湖。就在第一天下午,陡坡後上了稜線,祐庭卸下十幾公斤背包,走近崖邊,眺望山谷,遠方有浪搖的鐵杉林,倏忽間,一張密不透風的膜,裹住他,世界靜默,就連十三歲時意外摔破耳膜而從此住進耳裡那隻聒噪的蟬都噤聲了。他閉上眼,生命只容許也只需要這一刻,直到樹林的波濤奔來,時間才又緩緩流動。那天,他止不住地掉淚,感覺自己被大地洗滌成一個乾淨而全新的人。
後來結束出版社職務時,在總編輯引薦下,祐庭成為了剛從美國學歸的園藝治療師黃盛璘老師的助手。他們除了一起學習成長,同時也一邊開創園藝治療。「透過植物夥伴特性所研發的教學活動,目的在於讓我們的服務對象對它們有感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因為喜歡而願意帶回家,然後形成一種良好的彼此照顧、相互支持的關係。」
園藝治療非根治,而是一種更近於輔助性的陪伴扶持。植物有異同,就像人,所需各有不同。了解植物的照料方式,一如要懂得人有族群、年齡與能力,甚而身障、視障、聽障與精障等分別。治療師居中橋接植物與人之間剛好的相處模式,使植物獲得生長的驅力,讓人在創造幸福感的生活經驗中,重拾生為一個人的重量。

我願是一片土壤
「帶有生命訊息的植物與大自然非常巧妙地處理了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張力,它們提供了一個緩衝。就像帶著議題或挫折來的人,我們將治療設定的目標藏在相關任務底下,看似無關連、也不直接接觸問題,直到那個人從心有感而發了,我們再回應。」不論私下委託或單位機構,都經歷不少案例的祐庭從不把自己當神,他清楚自己的限制,做得到與辦不到的界線。這也是他一直以來不過度承擔,亦不使對方過分期待的不二法門。
人心是肉做的,祐庭身為一個園藝治療師,長年來,也為許多服務的個案所療癒。那些故事,有的離奇曲折,有的哭笑不得,心酸或沉甸,喜怒或哀樂,都是他人無可迴避的生命現場,所以難免觸動,總是有慨。憂鬱或焦躁,自閉或暴力,無論是否身不由己,祐庭以為茅塞的關鍵,往往不是迷失自己,就是不認識自己,就像他當年循著心理系的幫助而頓開,現在他所從事的,無論透過園藝或其它媒介的治療,無非都是在協助人專注地「找到他自己原本的樣子」。
我以為,祐庭乃至於每一個為園藝治療努力的人,其實都是在為教案對象的人生在種一個願望,但他卻說:「每個人自己就是一枚種子,只是有沒有適當環境去萌芽。我在做的工作比較像是在培育土壤,任何落在這片土壤裡的種子,都有機會長成自己真正的模樣。」就像所有存在地球上,且被命名的植物那樣。我暗自想著。
訪問告一段落,祐庭聊到日本榮格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某次在村上春樹的專訪中:「現代人普遍缺乏一種能力:安靜而深入地投入他人的能力。這話為我指出了一條道路,我做得到這件事,所以我很喜歡現在的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
祐庭金絲圓鏡框後的一雙眼神裡,光芒清澈,而我聽見的是:我願是那片種下每一個願望的土壤!
* 文字、攝影 / 陳冠良

「 種一個願望 SEED OF HOPE 封面人物」_ 蔡祐庭
園藝治療師,目前擔任「象山農場」管理人。
台大心理系。曾任兒童雜誌編輯。喜歡植物,喜歡人,臉書的自我介紹寫著:照顧好自己就是在照顧別人,共好人間就是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