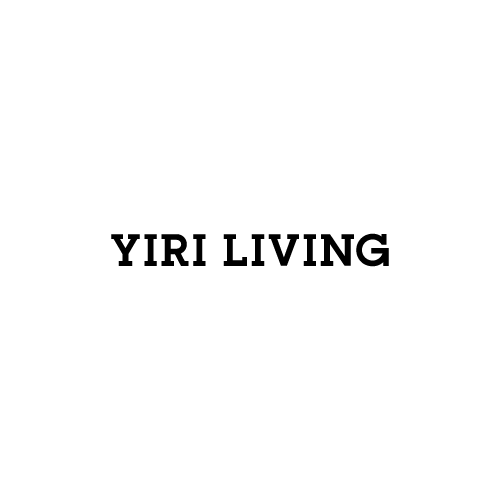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Silke Briel HKW
©Silke Briel HKW
這個文化中心有非常明確的策展路線,所謂世界文化,這裡的展覽就是以「非歐洲」的文化為主並且以學術性的策展手法發展內容,在柏林的藝術現場時常獲得內容很硬的名聲。而此際,正在展出的兩檔站在人類學家肩膀上的展覽也是極佳的案例,呈現了「世界文化中心」的風采。
在可以說是德國行政中樞的區域中,觀光客隨意漫步就可以抵達柏林總火車站、德國議會、各國領事館、布蘭登堡門和巨大的蒂爾加滕公園等知名景點,然而此區除了著名的漢堡車站當代美術館,在觀光客的主場景以外,有個名為世界文化中心的藝術機構(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也座落於此,這個機構作為美國贈與德國的禮物,甘迺迪總統於兩德時期在屬於西德的此地發表過演說。
在轉型正義這條漫長的道路上,德國近來慢慢的開始回顧起自身的殖民史,而名為 Spectral White (白色光譜)的這檔展覽,展出立基於德國科隆出身的人類學家 Julius Lips,於 1937 年在美國發表的研究《The Savage Hits Back or the White Man through Natives Eyes》(野蠻人的反擊或原住民眼中的白人),將敘事的主詞置放回被殖民者的身上,展出了許多被殖民的原住民所雕刻或是繪製的白人身影,有許多是作為紀錄之用,但能見到被醜化的特徵,如白人男性的嘴裡被鑲上凌亂尖銳的豬牙、無眼珠的白眼、相對於身形而顯得過度放大的生殖器等等,若試著想像製作者的妖魔化白人的動機,似乎嗅到某些警世意味,又或者是對於白人的恐懼投射。
 ©Silke Briel HKW
©Silke Briel HKW
當然在歐洲地理中心策劃這樣的展覽,回顧在 1937 年納粹德國還在處於種族主義以及法西斯的政治主張的場景裡,Julius Lips 這樣的研究發表與其說是反擊,更像是冷眼指向殖民者或者種族優越主義者的目光狹隘。當然,這樣的內容對於西方或許是一種反省,從這些介在可怖與滑稽的白人雕像看不出來可以辨別的高調仇恨,反而似乎只是呈現出被殖民者的日常抵抗。而我身為這場對話之外的旁觀者,最有感觸的,大約是所謂文明,或者所謂野蠻,似乎都只是一種相對的價值觀。在殖民者的眼中的野蠻人,將敘事主詞互換,或許也會將對方形塑為對於自身文明無知的白色野蠻人吧。
而與這間展廳相對的展覽 Love and Ethnology(愛與人類學),從展名很顯然地一樣是人類學的主場裡。展出奠基於一名人類學者 Huber Fichte(1935-1986)的系列小說《The History of Sensitivity》(敏感性的歷史),身為同志的 Huber Fichte 在七零年代,十分著迷於非洲地區的藝術與宗教,進而旅行於薩爾瓦多、聖地牙哥、塞內加爾達卡、紐約及里斯本,並在這些地區發展激進敏感性的烏托邦研究。藉由調查、男同志的親密關係、自我探尋以及觀察,最終呈現出民族學與西德戰後的新浪潮的美學面貌。而這次策展主要提出了一個問題:民族學的觀察以及德國作家對於非洲離散文化的感觸可以被重新還原嗎?而進一步的問題是:將自身投射以及同志性傾向作為研究工具的可能性與極限何在?
 ©Silke Briel HKW
©Silke Briel HKW
看到這裡已經起心動念想放棄的讀者不用沮喪,在這個宣稱要展出去歐洲文化的現場裡,好像又呈現出只屬於歐洲中心才會有的焦慮,但也藉由這樣的視角作為起點,與當代藝術家的敘事、文件、錄像、手稿的拼湊,有歷史文件和影像,相互輝映,我們像是透過了作者帶有某種美感作為濾鏡,折射出其時空下的靈光片羽之民族學殘像,或者他身為男同志對於黑人的崇拜迷戀之眼中的美學手記(他對於黑人社群的熟悉,捕捉了許多黑人社群的公共壁畫、塗鴉等影像描述)這些文件、影像、錄像、訪談所涉及的議題非常多元,從國家、性傾向到種族身份認同、和個別美學的形塑、七零年代藝術現場對於新浪潮以及非洲文化的紀錄,零歲而龐雜的多元並陳。
這個策展並未設定任何觀點,而我也無法組織出任何答案,但卻在這些近乎破碎如萬花鏡的敘事之中,經歷了不斷的辯證理解試圖組織的過程,而這樣不斷的辯證,無法獲得簡明答案的歷程與挫折,或許才是這個展出的企圖:沒有什麼是堅實的。我們藉著不斷的辯證與理解,或許能看到稍微清晰的視野,但那終究還是從我們的眼睛看出去的風景,但限制與可能性也都應許在這雙眼睛之上了。能看到多少、看得多清楚,都是自己的事啊。

 ©Silke Briel HKW
©Silke Briel H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