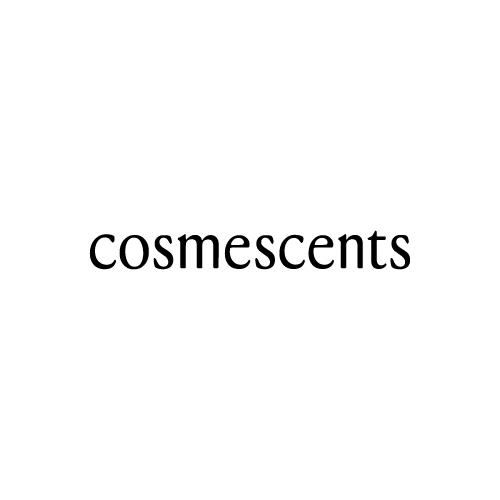迎向陽光,我們都放下 —— 四十歲女兒對父親的告白
只要聞到菸酒夾雜的氣味,就會讓我想起有關爸爸不好的記憶,
爸爸過去藉由菸酒逃避現實,這種氣味讓我很焦慮。
我對氣味非常敏感,小時候還沒聽到他、看到他,
聞到他的味道我就很害怕,甚至感到厭惡與恐懼,甚至會勾起內心深層的創傷。
我一直都在使用香氛,需要安定的味道讓自己感受到安全。
長不大的爸爸
賭博、酗酒、不負責任、一事無成,普世社會價值觀認為不好的行為都發生在我爸身上。在我的記憶裡爸爸是個長不大的男人;我爸是么子,我媽則是有很多弟弟妹妹,來自社會價值觀與媽媽所加諸的壓力,讓他在社會上生存很不容易,他不是「正常的老公」,更不是「正常的父親」,他什麼都不是,就是個天真爛漫、不切實際的男人。小時候的一次颱風天,爸爸一股腦兒地帶著我和弟弟去岸邊看大浪,把安全問題擱在一旁;他有很多屬於自己的小劇場小浪漫,但在現實裡這些是不被允許的,爸爸在社會框架的理性中是很難被接納與理解,社會適應不良逐漸被邊緣化,並開始借酒消愁逃避現實,酒後的行為對家庭造成很大的傷害。

圖1:飛比提供。
桃園大溪附近的水庫,飛比小時候,爸爸常常會在颱風前帶她與弟弟去看水庫洩洪。飛比後來用了這裡的漂流木做了一個跟爸爸有關的作品。
父母在我12歲左右離婚,爸爸有時候會跟我們住,有時候在外面自己住,面對外界壓力就會對家人發洩,這種狀態反反覆覆,總的說爸爸的出現對家庭是一種傷害,那時的我對爸爸深惡痛絕,非常排斥他,也因此很年輕的我就想組成自己的家庭來脫離這一切,「我希望他不要再來傷害我了。」
很快地我組織了自己的家庭,23歲那年我有了寶貝女兒。而爸爸那時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酒精中毒的問題讓他進出加護病房好幾次,肝功能失衡讓爸爸的臉色非常差,「臉黑黑的」,婆家的人因此有點擔憂肝病會傳染給我女兒。找得到的照片(圖2),是我女兒跟她外公僅有的一張合照。

圖2:飛比提供。
飛比女兒跟飛比父親僅有的一張合照,「因為爸爸肝不好,臉黑黑的,婆家擔憂會被傳染」總是不放心飛比女兒跟爸爸在一起。
沒能見到的最後一面
結婚之後,我才意識到在家庭中少了「父親」角色這件事,或許是因為進入到別人家庭,開始渴望自己原生家庭的完整性;但沒有因為這樣的渴望,而原諒我爸爸。爸爸晚年的最後半年時間,在中國一個人獨自面對病痛;我永遠忘不了在他要離開台灣時,在機場對我揮手道別,我因為賭氣不做任何回應,不揮手、也不看他任何一眼。最後他走了,真的走了,之後我接到的是他的一罈骨灰,在中國火化的。
不讓悲劇延續,面對女兒的父親
爸爸的離去讓我在往後人生不斷嘗試尋找內心的答案,對應家庭的方式,面對我的女兒,面對女兒的爸爸,以及我的婚姻狀態,恐怕是因為我跟我父親有情感上的遺憾、缺失與遺漏,雖然單親,但我努力維持我女兒與她父親之間的和諧關係,不給女兒壓力,不在她面前批評她的父親。我爸爸的事情是個悲劇,我盡可能不讓這種悲劇影響我的下一代,我們都是平凡的人,要強韌的活著。
至親離去,開啟一段自責的過程
爸爸離去,生活依舊;我開始歷經一段漫長的自責;自責過去年輕時的自己,因為期待被愛、期待家庭,但剛好父親就是沒有辦法給予我,我總是把我所需要的投射在爸爸身上,期望落空帶來的不諒解對爸爸有點不公平;最後因為賭氣,我沒能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
每一個結束都是新的開始,後來接觸了信仰,事情的態度有了新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面對過去的創傷,試著去理解、同理、原諒我爸爸;女兒長大後有了自己要忙的事物,我自己的時間也變多了,於是我決定再次進入校園。

圖3:飛比提供。
飛比人生中對爸爸的第一印象,「當時才滿月大,總記得有個笑臉的男人會很熱情地把頭探到我面前,後來長大後看到照片,才想起這段還是嬰孩的記憶。原來那個總是對著我笑的男人就是我的父親。」
這幾年我嘗試回想起過去有關父親的一切,常常內心會覺得這世上唯一愛過我的男人只有爸爸,小時候他打從心裡為我著想,關心著我、心疼著我,在他還沒有酗酒問題之前他是我非常懷念的爸爸。步入社會、接觸信仰,以及再次進入校園,遇到種種事情都讓我回頭去想有關爸爸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對家人所做的一切,諸如男人會用以抽煙、喝酒逃避現實的舉動,年近四十的我才開始慢慢選擇寬容以待,或許抽菸是人得以平衡、思考、放空、交際的模式之一?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都需要自己的空間,也都需要被理解。「就在半年前,我讓我爸爸真的走了」,不再將他綑綁在心裡,我需要放下他。
女兒像爸爸
有沒有一種說法是女兒比起兒子更像爸爸呢?我覺得我很像爸爸,喜歡親近大自然,喜歡與身邊朋友單純的相處,這些都是爸爸在我童年時影響我的,除此之外,我身上的感性特質也很像我爸爸,創作者天馬行空的想像、甚至是面對創傷時的強烈的情緒、有時候會很邊緣的性格......。

圖4:飛比提供。一歲的飛比跟爸爸,在六福村。
「有點想他。」
沒能見到他最後一面一直是我這十幾年最大的遺憾,這十幾年來我所做的事,進入校園等,似乎都在試圖開闢一條尋找有關爸爸線索的道路。我對爸爸的想法已經改變很多,「對他已經不是遺憾了」,開始有點思念他,而這樣的轉變也影響著我對世界的想法。很多時候我在所接觸的人身上看到我爸爸的形象,似乎看著另一個爸爸在跟世界互動,但最終他們都不是我的爸爸,我只能放下;我相信這世界上還是存在著堅持理想的人、每天滿腦子天馬行空的人,然後在這世界中頑固的撐著,最後默默犧牲。進入校園以及藝術的環境之後,我會這樣形容我爸爸: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但他很多時候比藝術家還要更像藝術家。

訪問的這天我跟飛比約在有戶外座位的咖啡廳,見到她的時候正在讀《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註1,這是作者露思.貝哈(Ruth Behar)拒絕遺忘的書寫,尤其拒絕遺忘痛苦的情緒,因此不斷地回首觀望自己發生的一切。傷心是一件很內在、很私密的事,你可以假裝快樂、假裝生氣、假裝興奮,但一個人的悲傷一旦發生了卻很難掩飾。傷心,是很珍貴的事。
沐浴在陽光底下,微風徐徐吹拂,樹葉被微風吹得唏囌作響,時不時還會掉落在咖啡桌上;訪問地點會選擇在戶外,是因為在大自然的環境裡,讓飛比感覺能夠更靠近父親一點。

愛,有時愛在心裡口難開,有時不知道怎麼去愛一個人,甚至是不知道怎麼去接受愛。
【 以愛之名.複方精華 】,內含主要精油有「茉莉」與「紫羅蘭」;綿密清新的茉莉,揉合馥郁華麗的紫羅蘭,花朵類精油提供你接受愛與愛人的能量,好好讓自己沈澱、穩定後,再次重新出發。
*註1:露思.貝哈 Ruth Behar,2010,《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群學出版,台北市。
-
飛比
目前是藝術大學研究生、藝術創作者,也是四十歲的單親媽媽,有一個正在念高三的寶貝女兒。
過去曾做過服務業、科技業、金融業、擺攤、經營服飾店等工作,也做過幾年影像工作、文化工作獨立策展人,身經百戰的飛比選擇在年近四十歲再次進入校園,透過學習與創作,尋找一生都在追尋的答案。 -
撰稿、攝影/豆宜臻
父親節,說一個有關父親的事。或許是因為筆者對父親的遺憾,想聽聽兒子和女兒,都如何形容自己的爸爸;親情很微妙,命中注定的關係讓一切充滿愛、歡樂、悲痛、憤怒與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