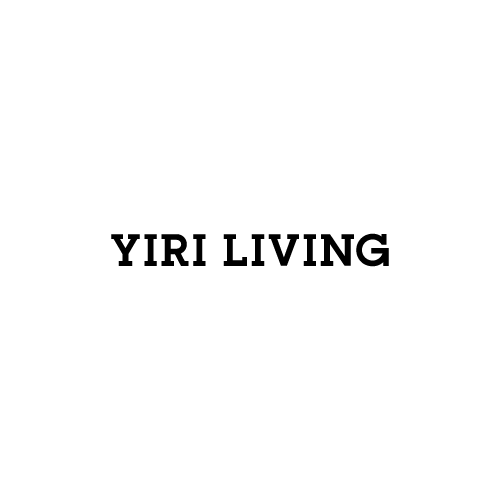對阿尼默而言,山本身,即療癒。「無論心情好或壞,應該都值得到山上走一走。那座山並不一定要怎樣的崇高或險峻,只要有很多樹木可以看就好了。」
文字、攝影|陳冠良
山中有藥
週末,彎彎繞繞的山路上,藍天淡藍,白雲積白,日光煦煦,無一絲燥感,一種夏天的前奏。
鬱鬱綠林間,泥徑還濘著,可能昨夜裡雨來過了。探訪「祕境」的人潮,一波接著一波,每雙踏來踏去的鞋,全免不了滾上一圈土色的花邊。
等待拍照的空檔,阿尼默也沒得閒,擅於觀察的眼睛,一刻未歇,四處遊巡於粗瘦不一,但同樣拔高的俊挺林木、一叢一叢熱鬧聚落或三兩離群的野花青草。
「你們知道颱風草嗎?」我們一臉懵懵,面面相覷。阿尼默指指一截臥地的橫木處,「相傳只要看它葉面上橫向的褶紋數量,就能預測當年將會侵襲的颱風次數哦。」
父親對阿尼默有過繼承中醫衣缽的寄望,打小就領著他攀山採藥,但阿尼默的天命畢竟是畫畫,中醫並非他的歸宿。「我跟我爸以前經常會採一種叫做『白馬屎』的藥草,它很普通,沒有確切功能,但可以幫助催化出其它藥材的最佳療效,讓它們在體內發揮更大的力量。大概就像B群那樣。」插畫畫了十幾年之後,阿尼默辦了一個以《白馬屎》為名的展覽,如此或許也不算全然辜負父親當初的著力栽培了。
小時候屢屢在山上遭饑渴蚊子吻得渾身紅豆子,而手採過的藥草都拋遺得零零落落,但阿尼默沒忘記父親教過的,「如果在野外迷路了,沒水喝,可以吃酢漿草,它無毒,水分多,有點酸酸的,也很容易找到。」
阿尼默對自然環境不陌生,甚至倍感親切,約莫便是奠基於那段與父親一同遍山尋藥的經驗,「我覺得『自然而癒』應該是大自然之於人類身體與心靈的安慰。」一如除非是立即性的危險,他不吃藥,讓身體透過時間,自然而然的修復好轉。就像中藥對他來說從不是治病的藥,「我爸會用排骨一起燉,很好吃,我滿喜歡的。」

丟掉不是丟掉,而是放掉
山那麼廣大,所以渺小的人們,總是趨之若鶩地丟垃圾——精神垃圾。
對阿尼默而言,山本身,即療癒。「無論心情好或壞,應該都值得到山上走一走。那座山並不一定要怎樣的崇高或險峻,只要有很多樹木可以看就好了。」他捨遠就近,習慣的路線是可以說走就走,位處居住地附近的知高圳或竹仔坑,「那裡有很多條步道,通常人都不會太密集。」
人們總是有所缺,但最不缺的,應該就是煩惱了。某一年,與阿尼默關係非常親近的母親摔了跤,在照護過程中的許多小細節,讓他眼見生命諸多的無奈與悲哀,而自身年紀漸長,看著母親的狀況,就彷彿預見未來的自己。那種逼仄感,就像被人壓著頭埋入水裡,無法掙脫的嗆溺,「其實每個人每一天都在更靠近死亡一點,很殘酷沒錯,但卻是必然的。」
於是阿尼默有了想逃的衝動,而想逃,是因為需要。「就像我吃過的便宜顏料,一入口馬上吐出來,連思考或感覺的時間也沒有,身體就直接反射動作。去山裡,即便只是郊山,就是身體在對我反應需求,我也說不上哪裡好,但身體就是覺得去一趟應該會很舒服。」他再舉一例,「我車禍開刀過,兩臀的大小有落差,偶爾一覺醒來,會發現一隻手掌壓在一邊墊高當作支撐,而那是在無意識的睡眠中所完成的舉動⋯⋯當身體感覺需要什麼,你本能的就會去滿足。」
若爬山是為了丟掉內心的什麼,恐怕只會原封不動地帶回家。「我比較常走可以一天來回的山。大概早上八點進,午後四點就不會在山上了。那樣一整天的體力流失,是累的,但過程中,我很自然的什麼都不會想,不管四周風景怎樣變化,整個人只剩低頭專注自己的呼吸與步伐,還有一路的泥土、落葉或樹根。」原來,丟掉不是丟掉,而是放掉。

那樣幾乎「什麼都沒有」的放掉,阿尼默以為某程度也很像畫圖。「有時畫到一個狀態,會變成純粹的身體本能反應。一個顏色,一種形狀都可能誘發我去回應,回應了就會有下一筆,而兩筆組成的東西又會引發第三筆⋯⋯慢慢的就會完成一幅圖。」他的「放掉」至此已轉變成不緊緊牢抓著什麼,才能夠繼續前進。當然,那是難得發生的,一旦來臨,便可謂是「創造力的偉大時刻」。
水瓶座的樹
阿尼默自承急性子,畫畫不先構圖底稿,不太執著細節,比較相信直覺下筆。意即,水瓶座男子的忠於自我,難忍被控制、被框架。然而凡事一體兩面,這樣的他就免不了被一個畫面中——無論場景、人物或主題的「敘事性」所縛所困擾。那大概就類似非常合理,也就非常無聊的意思。
「求快又想要有好的產出,現實上多少是衝突的。所以我大量製造,等時間過去了,不夠好的會被淘汰,還在的,就是值得留下的。」若阿尼默認定一張作品已完成,便不會再動念修改。因此,再不滿意已成定局的早期少作,他也不會持否定態度。彼時如何生澀,都是他不可抹滅的一部分,無關乎是不是成長了,而是他珍惜那個再也不能重返的曾經。
或許只有在看樹,乃至於畫樹的阿尼默是緩慢的吧。

住在一座環海的亞熱帶島嶼,季節分明輪轉,從來不乏豐富的植物生態可以親近。花很美,草清香,但阿尼默更鍾情的是樸質堅毅的樹木。「把樹開枝散葉的樣子放進繪畫的眼光中,其實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線條。因為一直為報紙副刊畫插圖,同時常常上山去看樹,久而久之,任何工作來,我都會先畫一棵樹。那棵樹,可能長在故事裡的人生活的環境中,也許象徵著主角的生命狀態。」
對於樹的姿態,肌理質感,柔和卻又粗礪的線條,如風雅的老者,阿尼默特別有感,「雖然會拍樹的照片,但好像也沒認真看過。我更喜歡實際現場觀看每棵遇到的樹的感覺,那也包含了當下的環境氣候與空氣。」與每棵樹木隨緣的相逢,聽來頗有「一期一會」的況味。那況味,亦教人想起阿尼默的台語詩繪本《情批》裡情意綿綿的那句:「假使有人對你表白,毋管佮意無佮意,請好好對待,因為彼是一條經過千山萬水,才會來到你面頭前的路。」
如果想像自己是一棵樹,阿尼默想化身「不清楚為何總是長在水畔」的柳樹,「我想要就自己在那裡隨風擺盪。」果然是棵很水瓶座的樹呀,「不過,比起泥土上面,我更在意泥土下面。我希望每天都能前進一點點,可以去碰到其它樹的根,接觸,然後對話。」此番想法,也許始於創作《情批》時,對樹的各種層面的思索;或可能起於幼年跟爸爸一起採藥草時,不要葉瓣不要莖,只擷土底的根。

變成一本冊
「我覺得樹木是會走路的,只是像流動的玻璃,很慢很慢很慢⋯⋯」阿尼默像是有枚燈泡在腦門上登愣一閃,「也像是一種不動的動物。」
或許,真是大地有靈,樹便有了魂。小時候,住臺中的阿尼默都會回靠海的沙鹿外婆家度過寒暑假。有一次,回家以後卻久病不癒,母親帶著他的衣服去收驚,「那位師傅說我被樹精嚇到了。」然而,在假期裡像隻野放猴崽四處玩的他,只是詫異,那人怎會知曉他有去爬樹?
與席慕容的〈一棵開花的樹〉:「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讓我們結一段塵緣/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不同,阿尼默在《情批》裡的樹,並非消極翹盼的等,而是「我較早是一欉樹仔/這馬是一本冊」,積極地來到每個閱讀的痴人手掌心,表明那「予阮踮佇你的身軀邊/蹛佇你的心內面」心跡。他詼諧地註解道,「你不來,我就去找你。」
熟識的人都知道,看似正經約束的阿尼默,私底下是個很好笑的人。當然了,那不過是其中的某一面,即便不是俄羅斯娃娃那般多重,也沒有誰是一塊實心的木頭。
「我其實不是一個那麼喜歡被觀看的人。」那「觀看」指涉是廣泛的,無論是外在或內在,阿尼默顯然更傾向於,亦需要保持適當距離。「比如寫散文的時候,即便內容是真實的,也會有所剪裁,不會全盤托出,如果必須說謊掩飾些什麼,那我寧可選擇不說。而在《小輓》那本漫畫集裡,不論是改編我自己的真實經歷,或虛構,就算有『我』的成分,也不會是原原本本的。那些人物角色出自於我,卻都是獨立的個體,『我』只能服務,不能干涉,甚至取代他們。」
在晨間的森林裡,沐在燦燦陽光、葉影斑斑下速摹一片繁茂林木的阿尼默,那不管喧嚷如何熙攘,心無旁騖而自成一個世界的專注身影,忽忽然又浮上眼前。

不去想自由,才能真正自由
創作人的瓶頸,或許與生活上的滯潮是連動的。
面對停頓,阿尼默從未懼於跳出舒適圈。他毅然出走,把自己放逐到陌生異鄉,念書學習,過日子。背離熟悉而安全的一切,可能有點極端,但那卻會讓自己的感官重新被打開,放大。「任何沒做過的事我都不怕嘗試。因為當我感受問題、理解問題,發現問題在哪裡的時候才能做出改變,設法解決,我需要的,只是時間。」
若遠走高飛是為了追獲嚮往的自由,「光想著要自由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困境了。如果我是一個拘謹的人,畫出了拘謹的圖,那就接受自己本來的樣子,才是真的自由。這麼想之後,反而畫得更接近當初的期待了。」回來以後的阿尼默,如是說。
自由不自由,只是一念之差。就像過著簡單生活的阿尼默,或許仍然不乏煩惱的事,但他已不會為了那些而焦慮,「找到一個屬於自己舒服的節奏過生活,就好了。」

若要畫一張圖呈現:遍布植物的一座小島上,住著一個生活態度豁朗的阿尼默,那應該是這樣子吧——遇上一場驟雨的他,無預警,但不慌不忙,隨手拔一片大大的姑婆芋當雨傘,就像小時候一樣。
阿尼默(Animo Chen)
畢業於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捷克布拉格應用藝術大學純藝術學系繪畫組碩士。作品面相多元多產,擔任過劇照師、電視與電影美術指導、動畫導演與十八年插畫家資歷,擅以文學式圖像表現,與文字相映,寓意深遠。作品常發表於各報文學副刊,為書籍繪製封面。在台灣及捷克舉辦過多次個展、聯展。出版個人圖文書多部。漫畫集《小輓》榮獲2020年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書展拉加茲獎青少年漫畫類首獎及金鼎獎,台語詩繪本《情批》榮獲2021波隆那書展拉加茲獎年度主題「Poetry詩類別」評審優選獎。
FB/@animo.chen IG/animo_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