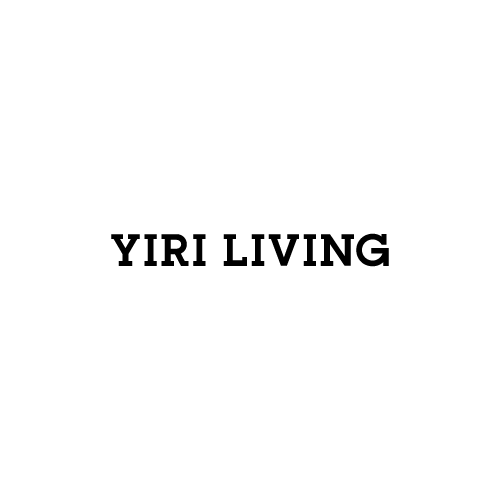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我們身體有一種『自療』能力,當有特別想吃的,即身體在發出訊號,你要抓住它,那是有道理的。不過,若是長期被人工味精摧殘,老想著美式或韓式炸雞就另當別論了。」—— 飲食作家 蔡珠兒
文字、攝影|陳冠良
野童年
端午甫過,熱氣還沒燒旺,就讓幾盆雨給潑熄了。那早日光昏昏,過午,天色更躡躡沉了一階。所謂晴好,本想黯霾天候招煩惹嫌,但蔡珠兒顯然不為這點小事犯愁,「其實我特別喜歡這種天氣呢。」約訪地點,位處深坑半山的宅邸。一身套頭無袖白裳,足蹬桃紅鞋的蔡珠兒,雖初來乍到,一見種類豐繁的綠栽植卉,忙不迭指認著這棵、寒暄起那株,興味盎然,彷彿滿屋子都是相識的老友們。
父親在台電工作,隨著派駐電廠的任務,而舉家搬到了花蓮木瓜溪上游的龍溪,即今時的慕谷慕魚。三到五歲的童年時光,蔡珠兒與童伴們就像咕咕咕的放山雞,每天滿山遍野到處跑,賣力玩。在天然的遊樂場,他們折葉莖摘果子扮家家酒,從來不缺材料。「那時就懂有一種俗稱酸甘蔗的火炭母草可以喫,酸酸的,很解渴。」後來即使遷進花蓮市區,寒暑假回埔里阿公阿嬤家的蔡珠兒,一樣還是可以去爬樹,跳下田邊的灌溉圳溝摸蛤仔,抓田螺,在有青蛙、螢火蟲的環境裡,開開心心當個野小孩。
「在兩千公尺的高山,雲來霧起,一片白茫茫,不看錶也知道已經中午。到了晚上,嵌著毛玻璃的格子門窗上會泊滿看似豔麗蝴蝶的蛾群,現在想來,還真像一場後印象畫派的夢。」花蓮與埔里在蔡珠兒的意識與身體裡,深深種下了自然的魂與植物的根,所以六歲搬至台北,前後住過三十載,她的歸屬認同仍是那最初即永恆的青山綠水。

用沙拉馴服夏天
略略摸索過陌生的廚房空間,繫起圍裙,配置妥食材,挑把適手的刀,廚娘蔡珠兒粉墨登場了。夏日燠熱,人懨懨,食慾寡靡,先甭提怎麼吃、吃什麼了,備餐時能少揮點汗才更添動力吧。不油不火,且不缺滋味的,非沙拉莫屬,其中又以沁絲酸帶辣勁的東南亞風味為尤。是日,蔡珠兒的沙拉無正式官方名稱,但越式魚露是靈魂。「魚露的鮮與腥很獨特,跟水果生菜搭配反而會轉成一種香氣。」
僅僅旁觀蔡珠兒做菜也是莫大享受,其俐落的行雲流水自不在話下,一邊聽聞領略每樣食材、每個動作的眉角意涵更是趣味所在。慣用的佛手瓜,原來是龍鬚菜結的果子,且帶刺的才新鮮,一如大黃瓜,所以叫赤瓜仔。端午假期,市場休攤,買不到佛手瓜,就以芭樂取代,若能得紅心芭樂更佳。芭樂切絲不切片,較易吸附醬汁,而絲不一定要細,但求均勻。剖半的檸檬,要選台灣的青檸檬,比起黃檸檬還多了一縷草香。正宗本土產的橄欖形洋葱,與同屬夏季恩物的番茄一樣會出水,務必最後再和入盆碗裡。且魚露也必須是壓軸,添早了,趨鹹變酸不說,香韻更會散逸殆盡。

蒜頭、辣椒、芫荽,檸檬汁攪融的黃砂糖,Sauce 調成,一切就緒。蔡珠兒指頭沾吮一口,輕聲一揚,「Perfect!」好奇問,比例呢?她鏗鏘地,「不用!比例在你自己的舌頭,酸甜鹹程度,相信自己的味覺就好。」誠如她也說過的,「做菜就會發現勺子湯匙都不如自己的手好使。最好的工具就長在自己身上,就像最好的分析儀在你嘴裡。」
「只要喜歡的,都可以加進去。毛豆、酪梨、蓮霧、美國杏仁、葡萄乾,各種堅果 ⋯⋯ 有變不完的組合花樣。在夏天,類似的沙拉我都做一大盆充作主食,當飯吃,舒服清爽,營養與纖維量也足。」一碟子青白點紅的越式沙拉,酸清辣爽,如何凶暴的夏天也被馴得服服貼貼。


身體都知道
《種地書》裡「三日不吃青,眼前冒金星」一句話便道盡了別人也許無肉不歡,蔡珠兒卻必然是無蔬難安。如連環套般,山中童年,是天分也是緣分,蔡珠兒已會將植物用眼睛拍照留存,長大識字了,再一一按名歸檔,而當她開始烹飪,由能食用的植蔬下手也就順理成章。
蔡珠兒對青蔬的愛意與需要,連在不甚便利的旅途中也不曾冷卻。人在異國,厭了館子的油鹹,想吃蔬果想狠了,逮到機會就動手煮上一桌,吃個過癮。「我喜歡蔬食,純粹喜歡它的味道,不是講求養生或養身。我也不信什麼春天要吃酸,冬天要進補,五行之類的事情。」她覺得好吃的東西必具有其作用。
「我們身體有一種『自療』能力,當有特別想吃的,即身體在發出訊號,你要抓住它,那是有道理的。不過,若是長期被人工味精摧殘,老想著美式或韓式炸雞就另當別論了。」我想,不斷對她釋出強烈波頻的,無非就是鮮翠蔬果了吧。身體會自我警惕,但也需要被善待。蔡珠兒曾嗜荔如狂,一次起碼三斤,鼻血當然沒倖免。吃到一個程度,身體反應太過甜膩,她接收到了,所以減量,適可而止。植物與蔬菜若作為對「身心健康」的象徵或方法,養在家裡的植栽,無論哪個角落,隨時一眼便獲舒坦綠意,若要悄吐心聲煩惱也沒問題,求一日「全植」尚且容易,但一日三餐要「全蔬」呢?顯然不費點心思不成事,還要淪為乏味無聊。
「用菜式去變化。早上來碗蔬菜粥或玉米粥,中午呢,就像今天這樣的越式或泰式沙拉,醒神醒腦,晚上可以吃地中海式的烤蔬菜,南瓜、茄子、番茄、茭白筍都可以,什麼都不用做,洗乾淨切塊,淋上橄欖油,烤好要吃時,撒上現磨的海鹽,陽台摘一把迷迭香,九層塔也不錯,有什麼香草丟什麼。」蔡珠兒摩撫下頦,眼珠骨碌兩圈,靈光流淌,一日全蔬,輕輕鬆鬆,豐富上菜。

家珍蔬食錄
生活行跡遍及倫敦、香港與台灣,蔡珠兒在每處都有一本親嚐的《蔬食經》,某些已然熬字成文,有些還釀在味覺的記憶裡,不斷醱酵。台灣筍,品種好,水準高,不同產地又各具風味,且關於筍的料理手法變化多端,精彩絕倫,甚至連日本京都也望塵莫及呢。「我正在訓練自己,看看能不能分辨出不同產區竹筍風味的細微差異。」
曾寫在《紅燜廚娘》裡的 Ratatouille,是先在巴黎友人家吃到的。其稱呼很多,地中海燉菜、尼斯燉菜或普羅旺斯燉菜,皆是其名,亦即《料理鼠王》片中的那一道。它就像台灣每個家庭都會煮的紅燒肉般,各有各的版本,她常常會自己做,但與電影不同的是,她才不管漂亮的擺盤賣相,通通融匯一鍋才是道地的,魂牽夢縈的絕妙美味。
倫敦令人拍案的,是印度菜。她最愛的一道 Aloo(馬鈴薯)Gobi(花椰菜),是在前菜時上桌的,應屬涼菜。顧名思義,馬鈴薯與花椰菜是主角,但就像寶萊塢電影裡的歌舞橋段,豈能少了陣容龐大的華麗舞群,Aloo Gobi 得用薑黃、番茄、芫荽子、孜然籽,以及小荳蔻等香料,一起煮到湯汁收乾。「我百吃不厭,也會在家做。熱的可以佐飯,當成餐前沙拉也合宜,不然也能搭配剛剛說的烤蔬菜晚餐。」
至於香港,可就厲害了。鼎湖上素,從廣州傳到香港,「這應該是素食界的佛跳牆了吧。」此道老菜,除了冬菇、口蘑、銀耳、楡耳等較名貴,喜冷的真菌類菇,還要黃耳、竹笙、木耳、白果、銀杏,與新鮮的蓮子、百合與竹筍等,簡直族繁不及備載。料齊了,做工也馬虎不了,每樣都須分別處理,有些要浸置泡發,有的要飛水汆燙,而部分本身無味的,也得先以高湯煨過後才能共冶一爐。這菜初始是一位和尚發明,廟裡用的是素高湯,變成高級酒樓菜後,便改以雞湯了。「香港早年還有人會做,但我吃到的次數不多,算是趕上一點尾聲。」那番消逝之味,若靠貧乏的想像力,恐怕連邊緣都搆不及,但或許可以期待有一天,蔡珠兒的巧手能召喚它還魂人間。
好好做菜,認真食蔬,都是愉悅的事,而做愉悅的事,即療癒,蔡珠兒從心所欲也讀書、聽音樂、看電影、下廚請三五朋友吃飯⋯⋯盡可能避免不療癒的,生活就充滿了療癒的可能。

在自然裡療癒,在料理中進化
不知幾時,滴滴雨水已婀娜了整片向晚的窗面。烏紫短髮,黑框鏡的蔡珠兒說著話,語調柔緩如羽毛飄蕩,咬字清脆,如珍珠潤亮的聲線裡,歷練俱足卻無一絲滄桑。
人生面臨過一些危機,經過許多次選擇與轉折,避無可避的寫作焦慮,甚至挺過兩次癌症的捉弄,如今的蔡珠兒不但一如既往地知性優雅,也愈發自在快樂了,「十年前五十歲,覺得自己都半百老嫗了,想做的事,想鍛鍊的技能,想寫的書,想學的菜 ⋯⋯ 一樣也沒成就,懊惱得很。」沉吟一秒,「廬山煙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一首蘇軾的偈語,表述了她跨過彼時惶礙,此刻見山還是山的心境。
「當然偶爾還是難免低沉,那時候我會回到自然,哪怕只是去陽明山,甚或走路到離家半小時的公園,我都可以像被重置清空的電腦一樣,再重新啟動。」想來不無道理,「自然」本來就是蔡珠兒從小的「原廠設定」呀,「我相信自然的療癒力量,那是巨大的,終極的。我想不只對我,對很多人,甚至動物也是一樣的。」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不同的辯證過程,並非想通什麼了就無憂無慮,明天有新的煩惱,後天有新的挫折,或對自己發生新的疑問。在那反覆的循環中,要懂得轉彎,軟點腰,神經該細時就細,該粗時就粗,多放棄些自以爲是,就少白白吃苦頭。但現實是,人即便不執迷,也不是時刻覺醒狀態的。一如蔡珠兒喃喃約翰藍儂的一句歌詞:「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生活就是你忙著做計畫之際,正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她仍會有所執拗抱怨,但同時也在努力試著把生活過得更好一點。
人生多像做菜,如蔡珠兒所言,「做菜絕對是一個經驗值,犯愈多錯,就離做好更近一步。」而人啊,其實也像是蔬菜,無論野菜或家蔬,都不能倖免在被加油添醋,過度調味的日常境遇中,忘卻了自己幽微的、清澄的,本來的味道。然而,蔡珠兒的另一席話又似乎不讓人那麼無望,「怎樣讓食材發揮本身原有的味道,讓它更像自己,但又煥發不同的光芒,這就是食物烹飪的藝術。」因此我以為,我們或許都有機會在正確的料理手法「調整」下,恢復甚至進化成更好的自己。
蔡珠兒
台灣南投人,在台北長大。台大中文系畢,擔任記者多年,曾赴英國伯明罕大學攻讀文化研究。熱愛植物、食物與做菜。曾獲第二十屆吳魯芹散文獎。著有《花叢腹語》、《南方絳雪》、《雲吞城市》、《紅燜廚娘》、《饕餮書》、《種地書》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