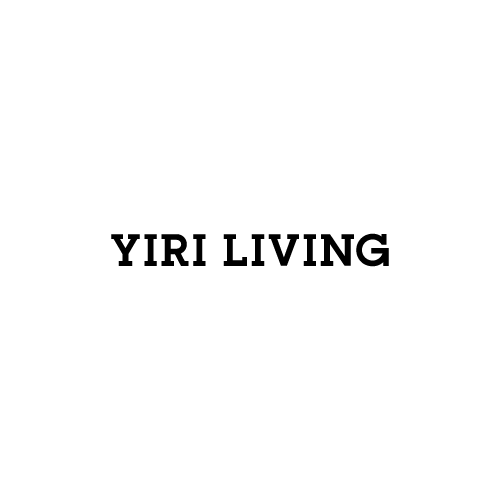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我覺得『自然而癒』就像做高度有氧的運動,專注集中到某個程度時會突然撞進一個安靜的真空狀態,那瞬間,好像什麼阻塞的都通了。」 — 黃書彥 Erik Huang
文字、攝影|陳冠良
SUNSHINE
冬末初春,乍暖還寒,傾盆的鋒面雨帶前腳剛走,滂沱的華南雲雨區接踵而至。
約定訪問的日子前,天天祈著雨快退散,後來絕望透頂了,竟怨嘆起陽光哪裡去了?是日,淅淅瀝瀝不見晴,然而,穿著淺赭色外套,一臉淨朗的黃書彥才轉進巷口,我們便頓然發覺了太陽的蹤跡。
「無為」的二十六歲
蘇珊.桑塔格說:「沒人透過照片發現醜。但很多人透過照片發現美。」同理申之,一張肖像如何「立體」,缺了喜怒哀樂,少了顧盼動作,透露的也只是一個人有意或無意被揀擇過的片面。就像我們看見社群照片裡的黃書彥無比精緻俊俏,卻又怎會意識他其實不那麼自信、不敢看恐怖片、面臨壓力時也會逃避等等⋯⋯身為平凡人的眉眉角角呢?又如,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健談,不但零距離感,還是非常有溫度的人。
「我是自尊心比較強的獅子座,以前很容易在乎別人怎麼看我。」率直的黃書彥坦言不諱。人既有先天條件,必也不乏後天因素,就像家庭環境的基礎形塑後,還是難免自我經歷的拿捏雕琢。大學時,「還好吧」是黃書彥常掛嘴邊的口頭禪,無論有意或無心,大小狀況,什麼煩惱,久而久之都在這三個字的摩挲下,變輕變淡,「可能也有點像是種自我訓練吧,加上後來的閱讀吸收,老莊思想裡的『無為而無不為』,去做該做的,順物順勢,順應自然,慢慢就成為我對事與處世的態度與原則。」
「本我」畢竟無法排除外界雜音干擾,獨善其身,但所幸還有個後來養成的「超我」在時時提醒著黃書彥,「雖然不能對別人的眼光免疫,但透過不斷的練習,仍有機會讓自己更接近無為的境界,放下許多無謂的牽絆束縛。」甫屆二十六歲的他,炯炯眼神裡沒有年少徬徨,閃動的是對一切自有主張,清澈的篤定。如今的成熟,當然不是憑空而來,就像鑽石不打磨不亮,成長總是要經過種種難關測試才能完成淬煉。
「我生命中遇過許多貴人,如果沒有他們,我無法想像自己現在的處境。」俗言道: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大學就讀會計科系,對黃書彥而言,就像田徑賽場上穿錯鞋子尺碼的跑者,奔得踉踉蹌蹌,摔到鼻青臉腫。想轉系又受限於成績,沒有興趣的不過就是另一個坑。念書念得超崩潰,常否定自己,一度覺得人生無望,那種挫折,使他愈加逃避課業。「後來我認識一個同學,是杭州來的女生。她的鼓勵、督促,甚至情勒,讓我直面自己的恐懼,進而認知很多事我不是做不到。她的陪伴讓我撐過了那段非常掙扎痛苦的時期。」書彥露出左臂上的刺青,是那杭州姑娘的名字,她之於他的意義與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動盪中的寧靜
人生是一場打怪晉級的電玩遊戲,一關破了緊接著又一關。
在女同學的助力,師長的諄諄善誘,兼及黃書彥自己的痛下決心,完成學分畢業後,學以致用,順理成章進入赫赫有名的國際會計事務所工作,本以為踏著前人路徑步步上階,飛黃騰達且看造化,至少安全無虞罷,豈料那職場模式的高壓緊繃與混亂失序,摧毀了生活品質,擰乾了身心餘裕,他內心所為何來的惶疑熊熊燃起。「事務所的環境,的確有人可以如魚得水,但不是人人都適合。沒錯,願意犧牲時間,投入精力就能獲得很好的報酬,可是一點都不快樂。」
彼時,壓力罩頂之際,捷運站返抵家門短短三分鐘路程,就可以乾掉一罐啤酒,雖無法強制將腦內的嘈鬧切斷電源,卻能將聲量扭小一點。真到扛不住了,索性心一橫,請一天假,就朝海邊疾馳而去。哪管天氣狀況好壞,只要看見海,下了水,遠離所有電子產品、社群信息,沒有工作進度的轟炸,獨自浸淫海中享受那寧靜片刻,一切擾攘就都被軟軟的撫慰了。「過度爆炸的資訊一從眼前耳邊拋開就很療癒!」他神情鬆暢愜意,彷彿在這城市的咖啡館一隅聞見了海的氣息。
原以為,海是動盪的,喧騰的,但其實不盡然。那屬於他棄絕塵囂,暫獲解放的靜海時分,讓人不禁連結起他說的:「我覺得『自然而癒』就像做高度有氧的運動,專注集中到某個程度時會突然撞進一個安靜的真空狀態,那瞬間,好像什麼阻塞的都通了。」
聽著,腦中竟竄出漫威電影《奇異博士》裡,卡瑪泰姬的古一大師如何狠狠開竅了傲慢冥頑的史傳奇情節。

衝浪手的等待
運動細胞不發達,小學 BMI 有點超標,沒跑過大隊接力賽,更遑論懷抱什麼職業運動員志願的黃書彥,卻是個熱愛戶外活動,不折不扣的運動迷。
「有人運動是焦慮不夠健康,有人為了壯碩身材而咬牙努力,甚至用營養食品或藥物加強。但我愛運動,並非追求什麼,不過因為那是自己感到最舒服的一種狀態。」所謂適得其反,如果運動偏執於某個目的而過度了、勉強了,對身體反而是莫大的負擔,甚至傷害。
山有山的擁戴者,水有水的痴心人,當然,更不乏兩棲雙修之輩。擅於也格外著迷衝浪的黃書彥,無疑就是個與浪共舞的海系男子。他聳聳肩,咧咧嘴笑道,「就像有人喜歡桌球,有人偏好羽毛球,爬山我實在不行,象山已經是極限。」
親水的他,小時候便是個帶著手臂圈在泳池漂著漂著就能安心酣睡的水男孩,如今更是一個人待在無垠汪洋也毫不恐懼,亦有猶如回返母胎般的歸屬感。退伍後,他在蘭嶼換宿打工過一小段時日。通常上午忙完,正午吃飯小歇,或跑跑步之後,他會去一處無人之境,那是礁石圈圍起來的潮池,潛下去可盡覽珊瑚群,豐富的水中生態,浮上來就敞著四肢像飄蕩在無重力的外太空。向晚了,隨意挑一座涼亭,聽音樂或讀讀書,黃昏餘暉,習風拂,眺著海色粼粼,那是一天中他最愛的療癒時刻。
海,瞬息萬變,這一秒不保證下一刻,它既納百川也能淹滅萬物,與其說黃書彥不怕大海,不如說他始終保持一顆虔摯的敬畏之心。「對我來說,衝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等待吧。在板上載浮載沉的等待過程,可以讓心沉澱下來。人生難免碰見困難,不停抱怨,除了把負能量丟給別人,自己也並不因此減輕痛苦,若只會愈講愈鬱結,那不如安安靜靜的等,慢慢就會了解到,情緒像一波浪來、一波浪去,不過是一個 wave,會流進心裡也會流出去。」
在書彥經由衝浪運動而體會的「情緒流動」意象裡,飽滿地充盈了一股被滌淨後的能量,從身體的撞擊,到內心的張弛,那能量,是汗後淋沐,是旱地甘霖,是雨後彩虹,是塵埃落定,是衝浪手穿出一堵浪牆後酣喘的深呼吸。只是想像一面海,一葉衝浪板,一粟若有所候的身影,天地何其廣大 —— 竟益發貼近黃書彥的身心何以能夠在時緩偶洶的潮浪之間被淘濯清淨了。


不只是剪髮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邊,不僅是句歌詞,也是黃書彥的盛夏寫照。不過一碰面就嘀咕最近好忙的他,持續緊湊密集的工作節奏,使得戲水弄潮的盼望在可預見的未來,顯得有些渺茫。
生命中有些挑戰無可僥倖避免,有些轉折卻是甘心情願的。念書到就業,黃書彥一路遵著世俗期待、循著社會價值而行,但就算是沒得回頭的高速公路,也還有岔出的交流道口。
轉換職場跑道剛滿半年的黃書彥,與美髮的因緣,其實早於大學時期在宿舍幫同學克難理髮便已種下。後來,身為基督徒的他,一次教會傳福音的機會中結識一位專事美髮的大姊,憑藉相同信仰的牽引,兩人一拍即合,無話不談,成為彼此遭遇麻煩困擾的救生圈,「有時候我去找她,頭髮還沒剪,就忍不住先訴苦,大哭一場。」盤點起來,她自然也是他當仁不讓的貴人之一。
任何「手工藝」活兒都不會是冰冷,缺乏生氣的,剪髮,原來不只是剪髮,在那坐下來,透過鏡子面對面的四五十分鐘的過程裡,或深或淺的交談,也是一種蕪雜心情的修整清理,「雖然一開始會比較怕生,但我還滿喜歡跟人講話,我覺得每次剪髮都是一次關係的建立,那其實是很有溫度的一件事。」相信光顧過黃書彥週末才開張的個人工作室都能充分感受其風格,「我希望來的人都可以好好放鬆,想說話就說,想休息就休息,在這段時間裡,就像剪了顆清爽的頭那樣,獲得一些釋放。」偶爾若不分身乏術,興致來了,氣氛對了,客人離開時無不微醺了呢。他頗感得意地,「一邊剪髮一邊小酌,也是讓人敞開心房的方式。」
在所難免地,也曾被質疑為何要放棄拿出來就略勝一籌的漂亮履歷,但比起受困於別人一點意義也沒有的認知框架,黃書彥更想要的是忠於自己。「以前在事務所工作,每天壓力山大,明明很累,腦袋卻不能放鬆,睡也睡不好。現在做美髮,不是不累,工作時段也很長,但因為熱衷,一整天的勞動下來身體很疲,心裡卻非常滿足。」然而起步晚,又從零開始,他很清楚與人比較只是徒勞,不如穩紮穩打練好基本功,盡快通過各項職技考試,在專業上獨當一面,唯有將狀態調整到位了,才不辜負自己的選擇。

DOLPHIN
午間,雨未息,但細了。降溫的空氣裡,略有一絲不刺骨,但沁膚的涼意。
偌大的游泳場,朦朦朧朧暈漾著一抹蔚藍光影,彷彿裡面住了一個夏季。池畔人影稀零,然而伸展著軀體熱身的黃書彥,青春緊實,就算人滿為患,約莫也是無法忽視的焦點。透過鏡頭,水中的黃書彥悠然自得,想起先前問過的:如果可以,他想當什麼海裡生物?他答,海豚。是呀,他就像活潑的海豚,親切,聰敏,那麼可愛。
黃書彥 Erik Huang
台北人,金融轉戰美髮業。目前正職於造型沙龍,週末有專司男子剪髮的個人工作室。熱愛戶外活動。天生好水性,對海洋充滿熱忱與嚮往,亦擅長水上運動,尤喜衝浪。
黃書彥 Insta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