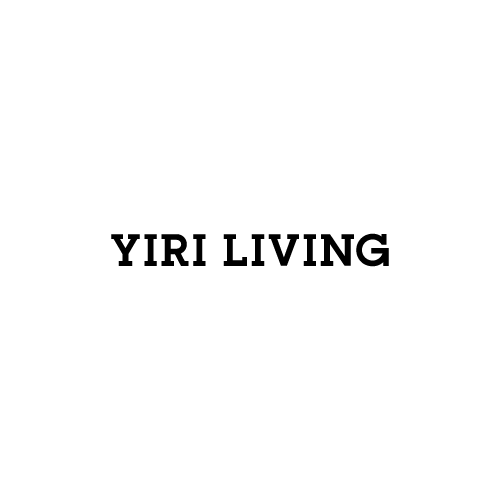自然的療癒,對我來說,應該就是被生活中的一些什麼觸動,而改變了對現下所承受的痛苦的看法。—— 封面人物專訪「故事工廠」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黃致凱
文字、攝影|陳冠良
偶然與必然
抵達「故事工廠」近正午,碰巧劇團的例行會議結束,霎時人聲沓沓沸揚,就像一台戲剛剛散了場。
亦步亦趨跟隨著引導,從挑高淨亮的辦公室,穿過黑盒子般的排練場,再到大片鏡面的梳妝間,我們像是握有自由出入後台的通行證,當然不至於劉姥姥進大觀園,但這兒看看,那兒瞧瞧,也是處處新鮮。不禁想,戲都是幕前的,而這幕後的空間裡,大概是孕了釀了痕跡了更多真實深刻的歡笑、淚水與汗水吧!
與導演黃致凱對坐的斗室裡,有一立面的書牆,一張大木桌邊,列隊般傍倚一排大中小型魚缸。一個劇本,如果閃耀的靈光是偶發的,想像力應該就是必要的條件了。
想像都是從填充缺乏而生的。黃致凱小時居住的大直是「台北的鄉下」,遍野蔓草,廢棄的木門、損壞的窗框圍起來就是種菜的園子,撿柴生火更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型態。家中不富裕,溫飽不易,哪敢奢求玩具,想玩就得自己找辦法!竹筷子組槍、紙箱折成棒球手套,塑膠袋加隻杯子便是掌中戲偶,取用有限的環境資源建構場景,模擬情境 ⋯⋯ 窮則變,變則通,物質或許貧乏,卻因此沒有限制,想像力解放了,創造得以發生。「真的是好快樂的童年啊!」若有一架時光機,他多想重返那個玩得自由無拘又花樣百出的自己。
人生際遇彷如一顆種子,總是偶然的播撒,卻必然在某一處萌芽茁壯。黃致凱在成長歷程的許多偶然中選擇了台大戲劇系(且是開山闢路的第一屆),而與恩師李國修的相遇,則讓他必然地成為了一個在劇場裡「說故事的人」。
「恩師李國修是影響我生命與創作至深的一個人。跟在老師身邊十一年,他從未當面褒過我一句話、一個字。或許他不輕易讚美別人,但在戲劇專業上、為人處世方面的教導卻是非常慷慨無私,完全不留一手,充滿愛與熱忱的。」未曾親耳聽見任何讚許的致凱,竟在恩師身後著手整理的訪談紀錄中發現了針對他「熱情」與「傻勁」的形容。以國修老師「嚴格的標準」來看,那完全不是評價,而已經是種肯定了。逝者已矣,無論驚喜或遺憾,他都只能報以潸然。

觀看的方式
生而在世,一具肉身皮囊,誰都難免磕撞。經過治療,才會「癒」,但凡需要療癒的,即有傷。傷了,髮膚可藥,那看不見、摸不著的心呢?
「我滿喜歡『自然而癒』這四個字。」對於不借助外援的順其自然,黃致凱覺得可以為自己準備三枚鏡頭。微距鏡,在一成不變的平淡生活裡也有不經意的小小美好;廣角鏡,運氣欠佳或面對批評時,看看身邊,每個人都自有難題,並不是只有你淒慘;哈哈鏡,用幽默對付不如意,一笑解千愁,哪有什麼是過不去的。
「當你認為有傷,就會想要療癒,若不覺得是傷,何需療癒?說穿了,不過就是一種轉念。」他憶起剛入行時的一次經驗,「有雜誌記者問我,劇場這麼辛苦,為何還要一直堅持?當下我真的是愣了好半晌才意會過來:啊?原來很辛苦!」一件事或某狀態的屬性樣貌,往往繫乎於怎麼看待或定義。一念之間,東南西北,天堂地獄,大不相同。
「自然的療癒,對我來說,應該就是被生活中的一些什麼觸動,而改變了對現下所承受的痛苦的看法。」人有執念才有了罣礙,而養魚乃至於盯著魚發呆,都是致凱化解的獨門之道。
喜歡動物的致凱,幼時,貓狗、螞蟻、螃蟹、松鼠、烏龜、蝦子、雞鴨、兔子、蠶寶寶、金龜子與白文鳥⋯⋯什麼都抓回家養,什麼都不奇怪。「到了一個年紀,開始比較能接受像養魚這樣『有距離的互動』,不是一定都要摸在手裡、抱在懷裡才感到踏實。」記得是妻子懷孕了,再也不能興致一來,裝備一揹,撇下老婆就自顧自去爬三四天的山。有次經過水族專賣店,靈機一動,既然不能親身大自然,那就在家打造一個小自然。養魚契機,由此始之。一如有人習慣看風雲變幻、聽竹林拍濤或佇望海浪往復,於致凱,觀魚時那種沒有目標,毫無目的,平和寧靜的狀態,多麼安定,極其療癒。
一旁的玻璃缸裡,顏色斑斕的魚仔優游,我非莊子也不是惠施,不能也不必知曉或分辨其處境快不快樂,然而,看著牠們彷彿無欲無求地擺來盪去,靜水流深,我想萬物單純,複雜的總是人心。

人類圖裡的「投射者」
散文集《二十分鐘的江湖夢》序文寫道:「我」字上少一撇,就是還在「找」。「對我而言,那一撇,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狀態。」致凱從不以為「找到某一個我」就是圓滿了,每一個階段都是不盡然類同的,全新的一撇。
在「故事工廠」創團作《白日夢騎士》中藉現代唐吉軻德探索內心幽徑,緊接著的《3 個諸葛亮》、《男言之隱》是愛情面面觀。來到似乎有點累積,但其實高度仍望不及遠方風景,對未來的患得患失,轉化成《莊子兵法》面對人生種種失敗的叩問。步入婚姻後的《偽婚男女》,並非為特定族群發聲,而是更全面地關於家、關於愛,關於幸福需要別人的同意嗎?《小兒子》的父子糾葛、《明晚,空中見》的母女心結,到《暫時停止青春》的反烏托邦寓言⋯⋯每部作品都是致凱一路以來,不因「找到了」而自滿,於是反覆尋得與拋棄的學習與成長。生命境遇層層疊疊,死守一個僵固的「我」,恐怕不過是一肩卸不掉的包袱,徒增拖累而已。
要暸解自己與認識他人同樣不簡單,免不了得借道一些捷徑,借力一點方法。
除了戲劇,較之占星、塔羅或紫微斗數,致凱傾向應用的「工具」是「人類圖」。「人類圖不預測,亦不負責未來,只談個人內在,相對是更科學一點的。」身為不易做決定,看世界的角度獨特又罕見的「四分人」,致凱摩挲著剃得精光的大平頭,像是個小困擾般:「我常常一句話說出口的同時,腦中會有千百萬個念頭在翻騰。」於是,他總不時要警惕脈絡的梳理,免得別人一頭霧水,連自己都被奔躍的思緒遠遠甩脫。
人類圖的設計,將人類區分為基本四個類型。致凱所屬的「投射者」,在定義上約莫是這樣的:「聰穎,擅觀察。經由關注別人的過程,研究分析,進而懂得自己。天性熱情,懂得善用每個人的能量,將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上。」姑且不論是否穿鑿,作為一名鋪陳各類角色光明面與黑暗面的編劇者、指引調度演員動靜與整體劇務的導演人,致凱不正正適得其所?若是一種天命,那麼,做戲的人,應該就是他的注定了。

劇場裡發光的恆星
宇宙,是一種在不同能量的交換中,無限創生與毀滅的循環。
人的內心也是一座小宇宙,有寂寞真空,也會爆炸喧囂。寥默與騷亂之間,偶爾失衡了,便是停止運轉的滯礙,應該要如何才能再次啟動呢?
「適時的陳述是必要的。講白了,就是要訴苦。無論感情上的障礙,工作上的困難,不要怕丟臉,一定要某程度地去陳述自己。那個述說的過程其實就在超渡痛苦。同一件事情,講十次也許沒什麼不同,但重複到二十五次,你就會認清現實,覺悟癥結。」致凱如是說。就像說故事是一種因果關係的爬梳般,當你把所有關節打通了,還有停頓不前的理由嗎?
「戲劇是一門與人有關的藝術。創造一個角色,若沒有看出他與世界的牽扯、與身旁其他人的羈絆,就找不出他的位置,就像在太空中漂浮迷航的塵粒,不知歸屬,沒有座標。」聽著,我不由得暗自以為,劇場其實也是一座深邃宇宙,而導演是太陽系中央那顆發光的恆星,用一個又一個故事的重力,吸引並標示出了所有行星的形貌與軌跡。
雖然劇場是一群人同心協力的合作成果,編導不應該是唯一的核心。但,一群全心全意投入做夢的人(無論演者或觀者),也必須依持一股堅定而穩定的凝聚力量,才能像致凱的座右銘那樣,將「把世界變成我喜歡的樣子」,轉換成「把世界變成我們喜歡的樣子」。
舞台劇的美麗與哀愁
《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裡,引用了黑格爾:「悲劇不是善與惡的衝突,而是善與善的衝突。」人生如戲也好,戲如人生也罷,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反之亦然,但也少不了哭笑不得的時候。沒有誰會自認是壞人,而當我們都自覺善良,那彼此扞格的究竟是什麼?尤其親人之間、朋友之間、伴侶之間,那些我是為你好的、你怎麼就是無法體諒的,有愛的,最是無奈難解。「不是每個黑洞都要填平。」致凱鏗鏘一句,道盡了愛的心甘情願、愛的是非難辨。
致凱的生命中有一種不後悔的愛,戲劇。「電視、電影、舞台劇,同樣是戲劇,我選擇了舞台劇。雖然劇場不如電視電影,無法有方便的媒介被廣泛傳播,但也因此特質,不會被取代,這個古老的行業不會被串流消滅。」
聊到劇場,致凱口罩上露出的一雙眼睛炯炯地,「我愛它的艱辛,愛它做一場少一場、每一場都不可能複製的可貴。一期一會,每個約定而來的人,在兩個小時裡只專注舞台上的一切,這是它無與倫比的美麗,同時也是哀愁。」因為那每一分一秒,過去就是過去了,再不復返。
「如果拋開票房因素,什麼是你認為『成功』的舞台劇?」我問。
「只要有觀眾因為作品而轉念,被拯救,就值了!」
曾有剛失戀的人,看完《3 個諸葛亮》,哭著感激致凱編導了這齣戲;失去父親的人,在《小兒子》的結局中補償了現實的憾恨;而某一場《與惡》的演出之後,有個人抱著致凱道謝,說自己就是劇中的應思聰 ⋯⋯ 那些被輕輕撩撥、深深撫慰的,都是屬於劇場人微小卻偉大的時刻!

黃致凱
現為「故事工廠」藝術總監。台灣大學戲劇系第一屆畢業生,磕頭拜師入李國修門下十一年,為李國修嫡傳弟子之一。近年著重「類型戲劇」的開發,以及舞台畫面的經營,作品風格多元,探究社會現象,常在嚴肅的議題中,放進喜劇的元素。除了原創外、改編、跨界皆多有嘗試。近年亦投身散文創作,2020 年出版個人首部散文集《二十分鐘的江湖夢》。故事工廠第 16 回,全新作品《一個公務員的意外死亡》,2022 年首演。
Facebook|故事工廠 / IG|故事工廠(@story_works)
故事工廠 / 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9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