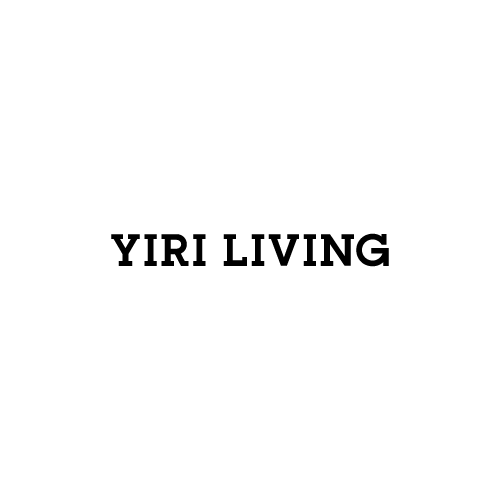撇除時間壓力的拘束,隨心所欲按照自己的節奏,無事打擾,徹底地擁抱一種集中而專注狀態,無論之與生活,或創作。大概就是兩人都一心嚮往的 A Better day。—— 封面人物專訪「Tu Xing/土星」工作室主理人 黃虹毓與彭奕軒
圖/土星實驗室、陳冠良
剛好的溫度
時序已秋,台南的熱情仍屬燠夏。說到熱情,才踏進「Tu Xing/土星」工作室,狗狗「吉利」便機靈地聞聲奔出。曾經是浪浪的牠,一身黑白相間的乳牛斑紋,親人不怕生,不過初相見,四肢一翻,便露出圓滾滾的肚腹討摸摸。
教授陶藝課的工作室髹著四面素白,簡樸無華的色調裡,伏著一股能量,就像尚未成型,等待被拉提、被捏塑的陶土,隱隱藏著什麼都可能的有機性。呢喃般的演奏樂音,低低在耳際飄,一個女學員俯身埋首專注於掌心中的泥胚,奕軒熱水沖著的咖啡逸香,虹毓新燒的一批作品正在屋後的窯房裡,從二百九十九度徐徐降溫著 ⋯⋯
「我們很幸運,離開學院後,獲得虹毓家人的支持與協助,所以跳過非常耗損的過渡期,順利銜接上工作室的經營。對一個陶藝工作者而言,健全的設備是很重要的事。」從二〇一九陶作教室的開辦,到二〇二〇三月於「林百貨」設置專櫃,奕軒坦言眼下種種不過是理想中的第一個階段。未來,會繼續將工作室外擴,透過教學大量化的過程、與在地博物館產生一些合作項目,最後再落實國際駐村中心的計畫 ⋯⋯ 這是他們希望在台南做到的事。對於奕軒的擘劃,虹毓謙虛地註腳:「不過那算是還很遠很遠的遠程目標啦。」

「男主外,女主內」是多麼八股的陳腔濫調,但對於奕軒與虹毓卻是再自然不過的適切形容。「奕軒是熱情的人,不怕挑戰,總是想把事情做好、照顧好。他很樂於與人分享經驗,也可以把我的作品包裝出色,『土星』因為他的運作而更趨完整。」虹毓靦腆地嘟噥自己好像在告白。而奕軒也聊了聊眼中的老婆,「她是標準的手作狂,很容易就投入手中的陶土或任何什麼東西,直到體力不堪負荷才會停。她總是在評斷自己,同時校正自己,也因此,她的作品比較難被取代。」時常處在創作中渾然忘我的虹毓,無暇分神,也分不了心,許多對外的大小繁瑣事務自然由奕軒一肩扛起。
他倆的互補性像是精細工藝的榫接,緊密而牢靠。當然,默契沒有天生,都是培養出來的,人都有隱蔽的稜角,不磨不會圓,若無協調哪有和諧?捏陶時看起來嚴肅難親近的虹毓,自覺是明亮而暖洋洋的橘色;而看似活躍玲瓏的奕軒自認是藍色,存在某種距離與警戒感,像一種會吸引生物的冷光般。「捕蚊燈!」虹毓靈機一動,例舉了奕軒曾在國美館展出的藝術創作。他們的一暖一冷,其實一體兩面,彼此在悠悠時光裡點滴成剛好的溫度。
光譜般的色階
工作室裡裡外外的層架上,除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各式工具,還擺滿了許多陶製物件,有些只是如胚胎雛形,部分輪廓具現還差妝色,有的已然細緻綽約。關於陶藝,無論陶瓷器皿或創作陶,都離不開一個基本元素:土。
「每個地方的土都有不同的顏色,而且,在燒過之後又會不一樣。」經虹毓一說才恍然,就像內行人與外行人的差別,看不懂門道就變成湊熱鬧,原來乍看深沉晦澀的土並不呆板無聊,它們也似光譜一般有其明暗濃淡的色階。「拿台灣為例,因為地形太豐富了,所以很難找出代表性的土壤。不同的自然狀態會形成各自的土層與特性,但原土的分布不是我們所想像的有個邊界,不會一個區塊就單純一種土質那樣壁壘分明。目前全島蒐集到的原土有二十三種,但這數字不過是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罷了。」奕軒更進一步補充道。
「在日本,不管哪裡的窯,採用的都是在地土壤。他們上一輩練的土是要傳承給下一代使用的。」虹毓不無嚮往地說。對陶藝創作者來說,「原土」是一個很根本的課題。在台灣的學院裡,買土是常態,也很方便,但完全不認識手裡的土,遇上品質不穩定,操作不順的狀況也就在所難免,屢見不鮮了。就是一個純粹的念頭:既然優良的原土是基本需求,那何不捨遠在天邊,從近在眼前的腳下的土地開始?除了讓提煉好土成為一件經常性、延續性的事,甚而據此去更深入認識安身立命的這座島。
從「土星」自身啟動的「原土計畫」於焉誕生。「這個計畫必然得打破侷限、拓展場域性才有意義,所以我們廣泛邀集了各方研究單位、工作室、個人陶瓷創作者提供所在地的土,當我們研究測試完成會回饋相關燒製數據給對方,他們再從而產出作品,這樣一來一往,除了形成互助循環的關係,同時也能較完善地建構台灣各地土質的資訊。」奕軒介紹完,虹毓緊接著便聊起:「我很喜歡台南六甲磚土的特質與顏色,但它也一度讓我滿崩潰的。六甲土捏起來的手感很黏但也很滑順,不過跟其他土結合時非常易裂,我曾經燒了三四窯皆告失敗,不過後來堅持試下去還是成功了。這種土本身很緊密,很實用,若不混瓷土,它在高溫下不吸水,在低溫中又可以透氣,很適合用來製作盆栽的盆器。像台東都蘭的土就很堅硬,窯裡的溫度再高都不會裂、不會爆。」
奕軒端捧出六甲土混用高嶺土,以絞胎技法手捏而成的盤子,那盤面暈染般漸層的色度,像等高線圖又似樹木的年輪,那一圈一圈彷彿沉澱累疊的色彩軌跡,是地形也是歲月,不規則,無序,卻充滿生命力。

本來的原色最美
「絞胎」可謂大自然地質的具象化,迭迭不休的色圈,漩渦般,猶如攪拌玻璃杯裡的拿鐵,又像是蛋糕捲的半剖面。「絞胎是源遠流長的一種技法,從唐代就出現了。雖然不是很困難,但非常麻煩,必須準備很多不同土種,並想辦法將它們攪在一起、燒在一起。」在學校時,虹毓看到各種回收重複利用的土糾擠在一塊挺有趣,亦欣賞那狀態與色調上隨機的變幻展現,於是便親手嘗試著做,所謂一試成主顧,她做著做著,耽溺於誠如「無為而無不為」那般,「刻意也不刻意控制」地纏繞出作品豐富的層次感,一路迄今。
不一定是崇尚,但應該類似偏執了吧。虹毓的作品從杯碗盤碟到茶具、花器與酒器,幾乎不上釉,讓陶土保持天生原色,至多為了現實上使用的考量(如食皿),在器身內部施以透明釉。「我偏愛土壤本來粗礪的質感,不喜歡土面被釉覆蓋,好像無法呼吸的感覺,雖然缺少釉料就無法遮瑕,但我覺得自然素顏就很美。」她笑眸瞇瞇,彷彿是對土壤的傾心表白。
工作室裡斷續迴盪著學員掌心拍土的聲響,時而鏗鏘,時而輕緩。好像靈感的泉湧與暫時乾涸。透過陶藝創作,虹毓捏出島土的姿顏,燒出土壤的豐色。她既形塑著土,也讓指間的土慢慢捏造著。「以前燒壞東西會很在意,但後來就比較看得開。只要不燒,土就可以反覆打掉重練。可以重來,其實是多麼難得的事。土真是太善良的材料了。」教學時,曾有學生表示:「拉坏好像婚姻,要分寸留意,小心拿捏。」似乎頗有道理,奕軒說:你怎麼對待,土就怎麼回應,捏土時若不慎碰摔,即便整回原狀,窯燒以後仍會或多或少偏歪一邊,受過的傷藏都藏不住 ⋯⋯ 想一想,是不是就很像存在嫌隙的婚姻,有所疙瘩的兩人關係呢?
一直以來,虹毓與奕軒關切並探索著各種原土測試數據、諸多燒製時無以捉摸的化學反應變化。陶藝,其實是很科學的事。他倆就像攜手在一片薄霧的林中,且思且行,一路上,有茫惑待解的挑戰,也有悄悄埋伏著的驚喜。但我想,凡是努力過的,怎樣的挫折與獲得,皆是至寶。

用一口窯的溫度煉色
一樣身為創作者的倆人,姑且不說焦孟不離,但肯定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儘管偶爾在創作上會想予人刺激感,但虹毓畢竟期盼每個接觸到作品的人都是舒服開心,減少負面情緒的。現在,她捏陶時或許依舊不自禁試探著體力極限,但已懂得接受當下的不完美,不逼迫自己達到想像中的某個頂點。工作與日常緊扣,讓奕軒懷疑過藝術與生活真的適合靠這麼近?太親近,會不會因為現實的壓力而相抵拖累?然而,比起那番意義的思索,到底,他更在乎的核心價值是:人跟人的互動所激盪出的動能,憑著那股子勁,願意資源分享,能夠充實地去做一件事,繼而創造更多更深的交流。
有相異,那齊相同的呢?大概就是二人都一心嚮往的A Better Day——撇除時間壓力的拘束,隨心所欲按照自己的節奏,無事打擾,徹底地擁抱一種集中而專注的狀態,無論之於生活,或創作。雖說在工作室馬不停蹄的忙碌中,那想望簡直是奢望,但疫情期間,一切怠速的情況下,他們反而鬆了口氣,一時間脫離長期緊張的運轉。疫情提供了一個餘裕,許多想做卻始終擱置的事,總算能周全了。
離開台南數日後,紀錄這場訪談之際,我想起那口大半個下午過去仍灼燙的窯。
一口窯,以一次一次熾熱又冷卻的溫度,燒煉出島土驚豔的色彩。那色彩,是催化,是淬煉,亦是歷練,仿若這座島嶼上多元族群、語言、文化與主張的共融並存般,那麼絢爛燦美,如斯目眩神迷。